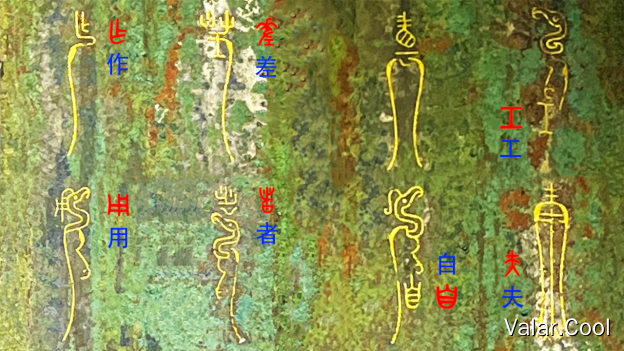在青州博物馆,最令人震撼的莫过于龙兴寺遗址出土的北朝佛教造像。这批造像形式多样,既有背屏式,也有单体圆雕。展厅中,佛陀与菩萨或并肩而立,或以坐姿与立像相互衬托,构成一幅宁静而庄严的图景。
这批造像的尺寸很大,北齐时期的佛、菩萨立像,很多都与真人等高。它们当年都曾通体贴金绘彩,袈裟上还绘有细密的“福田格”。历经千余年,仍有不少彩绘保存至今,鲜艳如初,堪称奇迹。
造像的神情和雕工同样令人赞叹。佛陀的面容典雅慈祥,菩萨则满身璎珞,衣饰华美。石雕的线条流畅细腻,将衣物质感与身体姿态表现得栩栩如生。它们共同散发出一种安详、平静的气质,让人心生敬意。
背屏式造像碑的构图尤其巧妙。在莲瓣状的背屏上,以高浮雕呈现主尊和胁侍菩萨。背屏上方是飞天、宝塔和游龙,下方则常见龙口衔莲,为两侧的菩萨托起基座。其余空间再用浅浮雕或彩绘填上头光、火焰纹等图案,将丰富的元素融于一体,营造出祥和庄严的佛国景象。